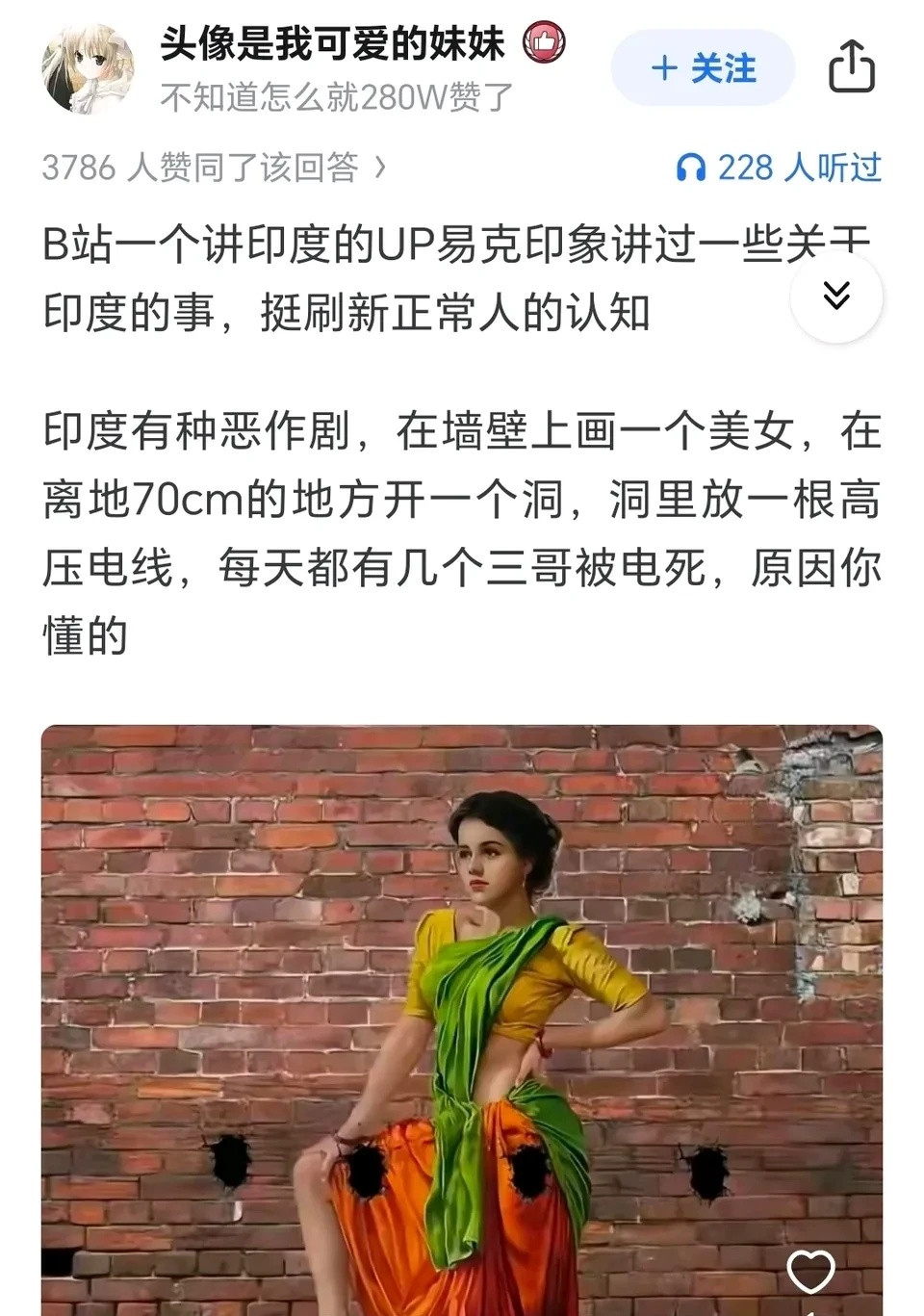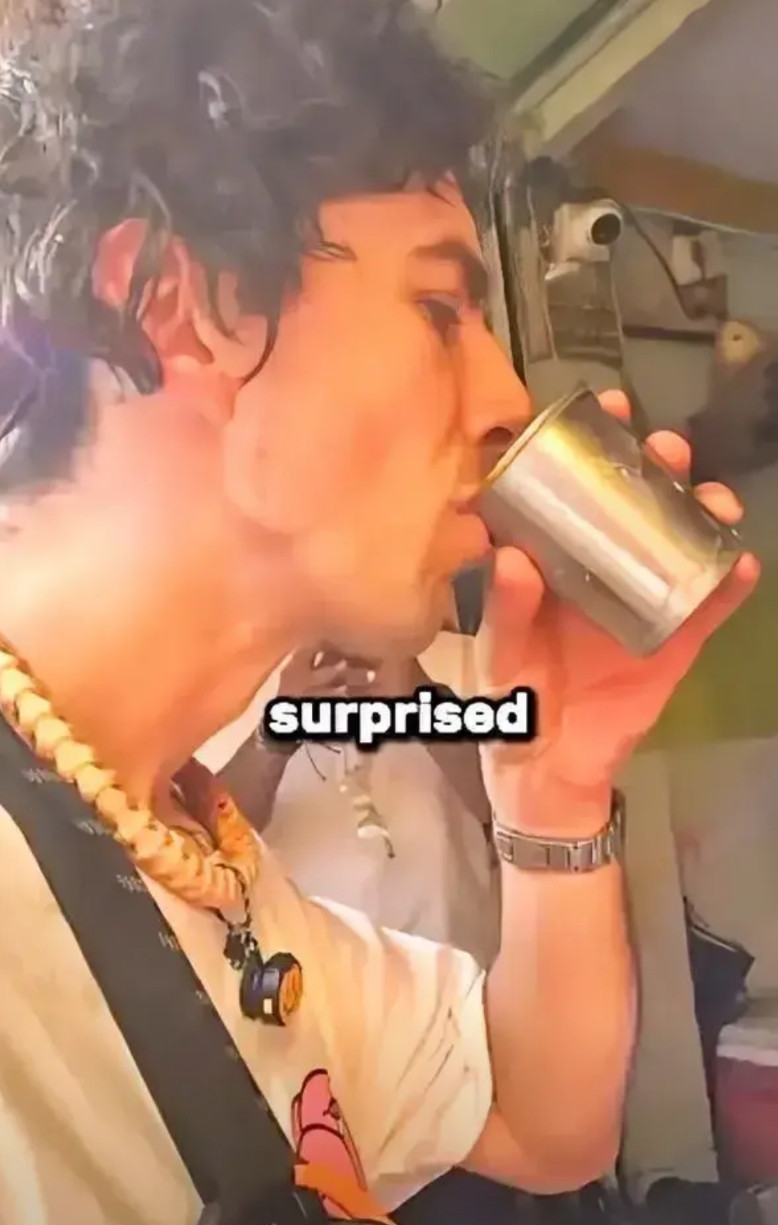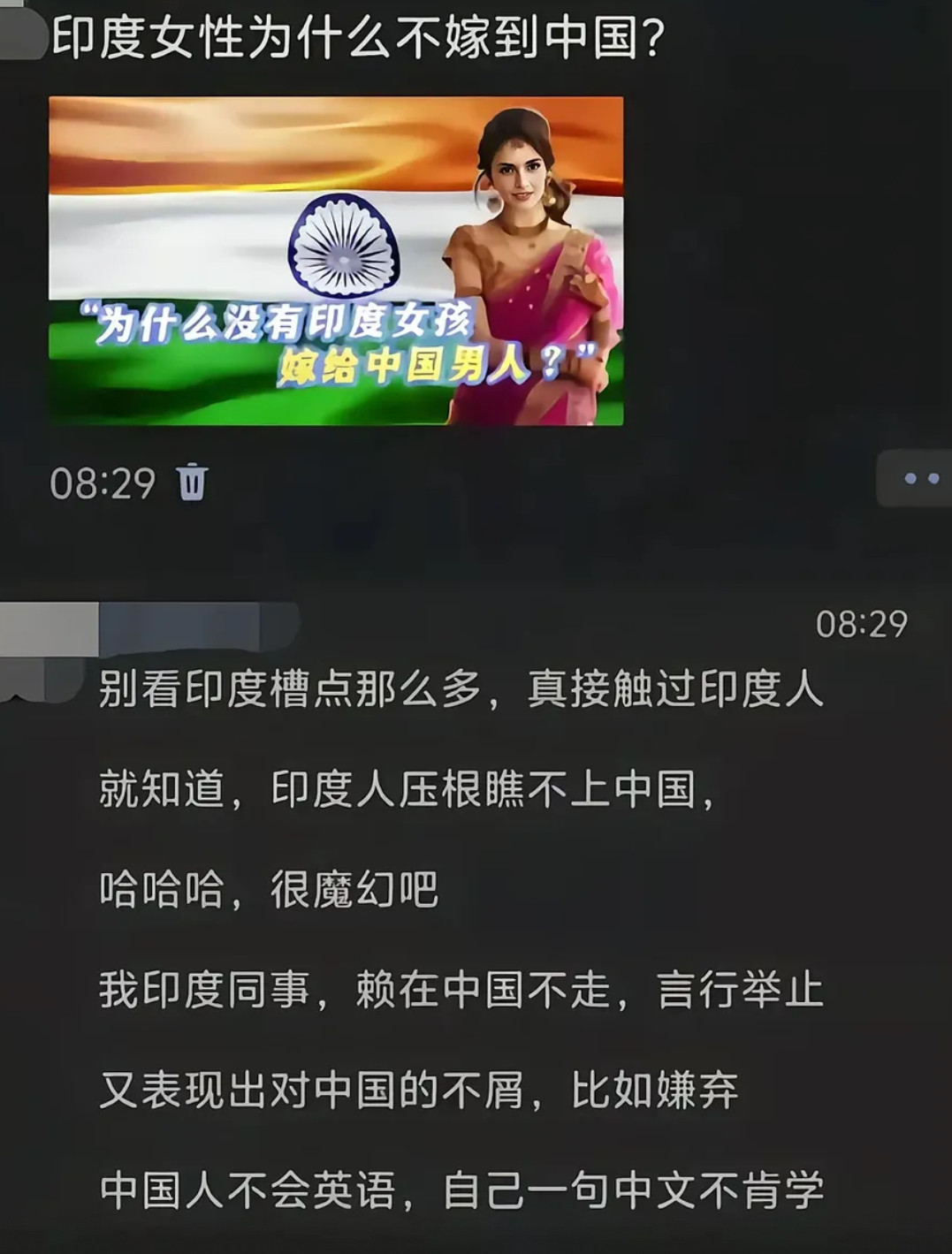左宗棠打下新疆最后一座城时,却意外发现城中竟有五千多印度人!而他们背后站着英国!面对这么多印度人,左宗棠的做法堪称千古!
1878年寒冬,清军主帅左宗棠收复和田后,察觉到城中异常。
众多操印度口音的商人活跃于市集,更有金发碧眼的英国人夹杂其间。
清点俘虏时,登记在册的印度人数量竟逾五千之众。
这些印度人为何大量出现在中国新疆?
其真实目的是什么?
成为迫切需要解答的难题。
新疆刚经历阿古柏之乱。
阿古柏原是中亚浩罕汗国军官,趁晚清内乱率军侵入新疆,建立“洪福汗国”。
其势力扩张离不开英俄支持。
英国尤为积极,派遣军事顾问,协助建立军工厂,并提供武器。
大量印度人正是依附于英国势力进入新疆。
其中一部分表面经商,实际则充当阿古柏和英国的眼线,暗中收集情报。
清军攻入和田后,市场内仍有印度商贩用乌尔都语交易,仓库甚至查获成箱的英制火炮零件。
俘虏甄别中更有身藏测绘罗盘、密写笔记的印度人。
审讯揭示,这些人白天装商贩,夜晚则秘密活动传递情报。
数千印度人滞留对战后新疆构成巨大压力。
本地粮食物资本就奇缺,新增如此多人口,极易引发动荡。
同时,清廷忌惮英国强大海军可能的武力干涉。
朝中对此分歧严重。
以李鸿章为首的重臣主张“海防”优先,认为新疆偏远难守,应尽快驱逐这些印度人以避风险。
左宗棠则坚决反对,深知新疆失则蒙古危,蒙古危则京师不安。
这些外来者如嵌入边疆的钉子,必须谨慎拔除。
左宗棠并未选择简单驱逐,而是制定了一套精细的治理策略。
首先,他派人深入市井摸底数月,将五千多印度人进行身份甄别。
约七成是普通商贩,三成则成分复杂,包含军火贩、工匠及英方间谍。
掌握详情后,左宗棠分而治之。
贴出告示,自愿回印度者,官府发放路费、派人护送。
愿留居者,必须迁往指定屯田区(如兰州附近),与汉人混住并学习汉语。
此举主要稳定普通商贾。
对于间谍及危险分子则予以威慑。
例如军火贩巴哈杜尔被“请”入衙门款待后,获赠银两并被暗示带话给英国:“大清疆土,外人不得擅行”。
巴哈杜尔惊吓之下迅速逃离新疆。
为规范管理,左宗棠在喀什等地设置“国际商贸区”,要求外商集中营业。
每个摊点必须悬挂刻有“大清光绪四年准营”的特制牌照。
另有专门的“市场巡检”监视,一遇哄抬物价(如抬高茶价的英商)立刻干预。
同时强制推行户口登记:所有留居印度人须到官府登记,领取加盖官印的黄色身份凭证。
无凭证者行动受限(如夜间不得点灯)。
正是通过此制度,查获一名自称“世代木匠”、实藏二十杆英制来复枪的印度人,其店铺被没收改为清军粥棚。
左宗棠的策略核心在奏折中一语道破:“驭夷之道,贵在刚柔得所。”
即恩威并施,既要展示底线力量,也给予合理路径,使其明白越界将自断财路。
这非常有效,短短一两年间,滞留的印度人锐减至不足一千,且行为更为规矩。
左宗棠的智慧源于对国力的清醒认识。
他估算与英国开战需耗费数百万两白银,这巨款却足够新疆军民饱食多年。
因此他选择用非军事手段。
本地经济竞争配合制度管理,最终迫使英国接受并遵守其在新疆制定的规则。
左宗棠处理外来人口的策略,深刻体现了其务实的治理思想。
面对复杂问题,在坚守主权底线的前提下,施行区别化管理,并通过发展本地实力来挤压非法生存空间。
这是一种将政治智慧、经济手段与制度约束完美结合的范例,为后世处理边疆复杂局面提供了重要借鉴。